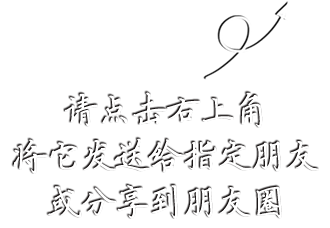◆ 冷冰
如果散文是一棵小草,一岁一枯荣,青了黄了,这是自然的事,没有关系,它的根在大地,明年春来,它还在,细嫩、蓬勃、茁壮,所有的鸟雀和光影都会眷恋它。鲁迅翻译日本作家有岛武郎的一句话:“人生的旅途,前途很远,也很暗,然而不要怕,不怕的人才有路。”路也是心生长的方向。
一个写作者是孤独的,但也是幸福的,我们发现万物之美,最后形成自己的思想,形成思想的过程,就是发现美的过程。
写作者最怕枯竭,写着写着无话可说了,写着写着觉得自己说的都是废话。所以我不主张做专门的散文家,一个人一生中没有那么多的情要抒发,写多了一类的题材,就会成为滥情、矫情和假情,写作者不妨去写写诗歌,去做一道美食,去旅行,去体验别人的生活,去烦恼、去痛苦,去爱。写作是自我和这个世界达成和解的一个过程,没有什么高大上,也不必妄自菲薄,这个世界纷纷扰扰,高明的写作者一眼望穿。
我们是一棵草,风一吹就会生长。丹尼斯·威特莱说:“只要你还嫩绿,你就会继续成长,一旦你已经成熟,你就开始腐烂。”一个写作者要警惕那些长期的规范式样的训练,那些写作的条条框框,那些形容词,那些摘抄,化肥用多了,土壤就会板结。
越是全民写作的时代,越要锤炼散文的品质。
散文是什么?巴金先生有一段话:“只要不是诗歌,又没有故事,也不曾写出什么人物,更不是专门发议论讲道理,却又不枯燥,而且还有一点点情感,像这样的文章我们都叫作散文。”
散文的范畴实际上是缩小了。散文就是这样,自由的、散淡的、有情的随笔。语言是重要的,思考是重要的,情感更是重要的。一位优秀的散文家有能力吞进庞大的信息和情感,经过消化和反刍,分泌出属于自己的认知。这种认知就是思想的生长,也就是散文的生长。
真正优秀的散文,都是真情所至。有温柔的内心,易感,求真,而非机关算尽。真正优秀的散文抚慰我们,但不取媚读者,它来自本心,激发读者身体内部的每一次感动。静水流深而又荡气回肠,天马行空而又细致入微,有钝感的重量,饱满,讲究而不矫情,有教养而不卖弄。散文可以向外,但关键是向内的,它不太是快餐,而是一种隽永,有一种安静的品质,是要在天地寂静的时刻去读的。
真情之至也是生长,他是沟通作者和读者之间的桥梁,写散文就是希望在第一时间对刻在我们心头上的遭遇给出反应,要和真像、真实和现实主义发生关系,否则,每天写那么多,都是空谈罢了。
人生的真实和虚幻,天与地,时间和空间,我们一直在对话,与自己,与自然,与现实,与心灵。小威廉姆·E·多尔说:“让我们共同漫游,向那’产生于上帝笑声的回音的,没有人拥有真理,但每一个人都有权利要求被理解的迷人的想象王国’前行。”
《散文》杂志的观点:“表达你的发现”,以此而解,万物都有文章的属性,比如水有水的纹路,山有山的肌理,纹者,文也,彩绘之则为纹。写作者要做到的是善于表达了你的发现。
在共青城起来跑步,我在珍珠湖边看到一棵树,上面停满了近百只乌鸦,日出之时,一批乌鸦向鄱阳湖飞去,又飞来一批,一批又一批,那棵树仿佛是一个跳板,乌鸦们乐此不疲,使我想到南极那些低头下水的企鹅,有趣之极。我在想,共青城给乌鸦留下了一片樟林,建了一个自然的社区,这些吵吵闹闹的鸟,为什么第一到共青就安静下来呢?
路人司空见惯,没有人停下来看它们一眼。写作者却出现了,他们善于思考,白描也好,赘述也好,关键在于思考,思考往往是最精华的一笔。我的思考和你的思考一定是不同的,思考的深度决定了写作的高度。
表达既是语言的训练,也是思维的训练。人往往只关注自己感到愉悦的东西,而忽视其他的东西,我们常怀一心,悲悯、热爱,细致入微,渐而入深,就能拓展我们写作的广度和深度。
新一期《散文》有一段话,摘抄如下:“午后,一个老人和他的螃蟹,站在龙山小区的路上,吆喝起来,我看到他每吆喝一声,肩上的扁担都会在风中向下倾斜一点,篾筐里的螃蟹就会挤挨着,骚动不止,我不知道这个下午,会有多少螃蟹离开——才能让这个老人完全安静下来。”
这是一个场景,一段普通的白描,只一个小包袱,语言平实中透着趣味。写作者最难的是把我们那些枯燥的生活,生动有趣地表达出来。
散文有多种可能的生长性。但不管如何生长,一定要有温度和光亮,一个散文作家要有情怀,有学养,有志趣。散文是光,你的一点点阴郁在散文里都会显现无疑。
在这个世界上,在生活中,人类最不能善待的就是自己的心了,我们活着,那些幸福感一再远去,看不见灵魂去了哪里?为了内心的安宁,我们写字,蚂蚁搬家,在心里盖一个房子,和那群乌鸦一样找一棵树,聚一群人,灵魂相近,趣味相投,也许,我们把它们记录下来,心中的幽灵就不会那么痛了。
阳光好,喜欢在有阳光的日子写字,仿佛是天底下的那一棵草,在不动声色地生长,猛烈地生长。
(以上均系在九江市文联2020年《浔阳江》笔会上的发言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