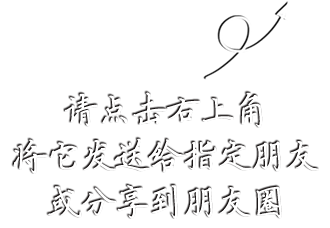■ 刘枫
犁耙车耖,这些不能开口说话的农具,让我们在收获作物的同时,也收获生活的真谛。
我们家乡的人相互交谈,介绍自己时,有句口头禅:“我是个盘泥巴头的”,即种田的人。这话说出来轻轻巧巧,其实,盘泥巴头,没有犁耙车耖,玩不转。
我的记忆里,犁有两种。一种是木犁,一种是铁犁。木犁,也是铁木结合。用天然有弯度的硬木做犁弯,前端是犁鼻,挂牛链;另一端,楔入犁底。犁弯弓部有一道横梁,与犁尾相连。犁尾是一根直木,顶端是天然的一个弯把,便于犁的掌扶。直木下端,分别是生铁铸的犁头和犁耳。铁犁与木犁的构造差不多,只是全部由生铁铸成。犁地时,前方动力牵引,犁头吃进土层,犁头带起泥土顺着犁耳的弧度翻过身来,将带杂草或是作物根兜的土层翻过身来,沤成肥。在表层土与下层土互相转换中,庄稼就获得了一茬又一茬的生长机会,得到需要的养分。
犁翻过来的泥土,呈条状排列,一圈一圈,有图案美,泥浪翻滚,又有动态美。若是水田,泥起水溅,原本藏在泥土里的泥鳅,被翻到上面来,有些就被人捉了,成为下酒菜。
种庄稼,要把犁起的土块弄碎。这时,耙上场了。
两块厚达1寸多的木板,接上两根横木,组成一个长方形,是为耙厅。两块木板上凿出洞眼,装上生铁铸的耙齿。耙齿安装在耙厅上,有一定的倾斜度。斜度小了,耙齿近乎直立,牛难拉动。斜度大了,耙齿太飘,吃土不深,不能破碎土块。
耙土时,站耙特别有讲究。前面犁起的泥块高低起伏,耙过来时,就会上下颠簸。牛在前面拉,人两脚分开,站立在前后两块横板上,一手抖着牵牛绳,一手抓住后横板上系着的一根绳子,确保在耙的颠簸中,人站得稳,不摔倒。在耙到比较大的土块时,人的前脚用暗力下压,耙齿就往下深扎,容易把土块破碎。
田地在一轮庄稼的种植中,墒畦轮换,难免会出现高低不平。犁过耙碎的泥土,不平整,种庄稼不好管理,也不利于水的涵养和保持。这时,就需要用耖来耖平,同时将泥土弄碎。
一段质地结实的树木做成“耖厅”,两边配上辕头,以便铁链牵挂;耖厅正中竖一根木桩,为把手,便于打耖的人掌握耖。耖厅下面则是一排耖齿,以前是用硬木做,后来也用铁质的,耖田地时,全凭耖齿搬运田地里的泥土。
打耖是衡量一个种田把式的技术活。下耖之前,要对整个田块全面观察,哪里高,哪里低,高处的土要运到低处来,这样才能使田地平整。
把式好的行家,牵牛走到下耖的位置,耖把低放,耖齿兜住泥土,驱牛拉到低洼处,耖把手扶起直立前倾,耖齿兜来的泥土倾倒下来,填平低洼。几个循环,田地一水儿平。技术不到家的人,往往找不好下耖的位置,反复兜空圈,人家看了,就会笑话:“怎么,你在带着牛唱戏啊?”
种双季稻的水田,早稻的禾兜,犁起的泥土不能完全压实,在田里横戳戳的,插晚稻秧时不方便,也不利于后期的管理。有些稻田本就有水,土质松软,也不须用犁耙,可以直接弄软了插秧。我们家乡是用一种叫着“钉滚”的来打田。
钉滚,一段结实的横木作滚心,楔入结木的齿片。横木两端装上耙厅一样的“钉滚厅”,厅上居中位置,用树木装上带靠背的座椅。滚心也有用铁制的,上面焊上铁齿。用钉滚打田,牛在前面拉,人坐在靠椅上,吆喝着牛,很神气,比扶犁站耙抖耖,那舒服不知多少。
以前庄稼人往田地里送肥运物,除了手提肩挑背扛,最省力气,见效最快的,便是用车拉。江南乡下,牛车可是运输的大力士,猪牛栏里沤的粪肥送到田地里,堆得像小山的稻草从田坂拉回到场院。牛车是木轮,牛拉着,在田间土路上,吱吱呀呀,很远就能听到车轮毂摩擦的响声。后来有板车拖拉机兴起,老迈的牛车就隐藏了踪迹。
庄稼离不开水。枯水季节,池塘库堰水量少,要将水引到高处的田地,就要用上水车了。水车,用杉木做成凹形的车身,下层薄木板为边墙,为车槽。上层木条有规律排列,为车窗。上下层之间置长条形木板。车头车尾都装转轮,转轮上楔入轮齿,用耐腐的木板做车片,一节一节龙骨,互相咬合。转轮滚动,轮齿带动龙骨,车片依次下水,将水带进车槽,由低往上,流进田地里。
水车的转动靠人力。一种是脚踏。在车头用两竖一横的树木扎好架子,车水时,人的身子趴在横木上,双脚踏着水车的轮片,一上一下,轮子带着车片滚动,提水上来。还有一种是手拉的,车滚轮的长轴上装上小横木,用车拐套住,一来一往,底下的水就随着水车上来了。
收获的稻谷,晒干之后,要入囤进仓。这之前,要用风车把谷扇干净。
风车,四根直木做成脚,一头是圆圆的车鼓,鼓里装转轮,配扇片,外置铁把手。一头是车身,上置车斗,前是出风口,风口内侧有一小出口,靠人站的一边下置一大的出口。扇谷时,摇动转轮,叶片呼呼生风,碎稻草和瘪谷从前出风口吹掉,不够饱满的谷粒从内侧出口下来,只有饱满的谷粒,才能堂堂正正从大出口出来,进到稻箩之类容器里。然后,过秤,进仓。
对于收获的颗粒类庄稼,风车就是一个裁判。当然,风车在执裁时,起作用的还是人。人用力大,转速快,风力就大,留存下来的饱满果实就少了许多。而转动风车轮时,用力均匀,风力适当,裁判就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