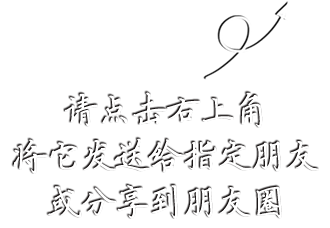■ 陈林森
葛亮是原籍南京的香港小说家,其作品风行于两岸。莫言称他是具有超人禀赋的青年才俊,聂华苓说他的作品令人“惊艳”。我特别欣赏他的描写,可谓字字珠玑,穷形尽相,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审美感,并且内涵丰富,耐人寻味。
葛亮的中篇小说《书匠》(原载《人民文学》2019年第12期)通过老董和鹿简这两位“古籍修复师”的故事,赞扬了中国传统的工匠精神,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小说的节选成为2020年全国高考Ⅱ卷文学作品阅读材料。下面是从小说中信手拈来的一段描写:
我们两个都没了说笑的兴致。人是越来越少,两侧的房屋依山路而建,尚算整饬,也很干净。但红砖灰砖,都看得出凋落。毕竟是在山上,看得见经年湿霉和苔藓灰黄干枯的痕迹。教授终于说,哎呀,歇一下。
这一段写的是欧阳教授带“我”(文学博士,小名毛毛)去拜访“书匠”鹿简老太太,他们乘坐小巴,停在半山腰,然后步行上山。上文已经写到爬山的艰辛:“欧阳教授毕竟年纪大了,终于气喘。我替他背了包,一边搀扶着他。教授这时候有些服老,说,这路走的,像是去西藏朝圣。”于是两个人都没有说笑的兴致。这说明不只是年老的教授,而且年轻的毛毛(大名毛果)也感到了跋涉的受累。接着写环境,人越来越少和建筑物的凋落是相互配合的,间接表现这条山路走的人不多和攀登的艰难。教授终于受不了,要歇一下。
“哎呀,歇一下”这句话,非常贴切地表现了老教授当时的语态。“歇一下”是祈使句,是教授要说的基本意思。补出主语就是“(我们)歇一下”。主语为第一人称的祈使句,表示(希望)说话人和听话人将要进行某种行为。第一人称的主语经常省略,口语中尤其如此。这是一般的语法特点。作者在这个祈使句前面加上“哎呀”这个感叹词,就使这句话生活化了,有累得受不了的意思,也有迫不及待的意味。我们可以说,教授发出“哎呀”的感叹,并不是主观上要表达某种意图,而实际上却包含了很多的言外之意。如果作者仅仅写“歇一下吧”,那只是叙述;而作者写成“哎呀,歇一下”,就成为了描写。这个素材可以作为初学写作者的教例,让他们借以区别叙述与描写。叙述只是记录事件,交代过程;描写则要再现生活,传递更多的内涵。“哎呀”这样的感叹词是脱口而出的,最符合当时当地的情境,是人物生理和心理状况的外化,甚至还包含环境的某些因素(从下文看至少有一个适合坐憩的台阶),有丰富的内涵。孙犁的小说《荷花淀》中也有一个经典的“哎呀”,是写妇女们去探夫途中,在白洋淀遇敌时,一个妇女脱口而出:“哎呀,日本,你看那衣裳!”表现了妇女的震惊和恐慌。如果写成:“那是日本鬼子,你看那衣裳!”固然更加理性,但生活的原汁原味也就荡然无存。
把书往前翻,在教授出门前还有一段描写,写教授与太太的对话,表达教授临时决定带毛毛去看望简时,向太太辞行:
然后对太太说,晚饭不吃了,我带毛毛去一趟上环。
欧阳太太正端了一钵杨枝甘露,叹口气说,你呀你,说风就是雨,可有半点长辈的样子。今天可是大年初三,你也不问问人家在不在。
教授说,怎么问?她手机都不用,电话不爱听。现在发电邮恐怕也来不及。
欧阳太太追上一句,好歹我辛苦做的甜品,吃了再去。
教授拉着我,头也不回地往外走。
这段描写可以看出教授的决断,太太的唠叨和对教授的关心,对拜访简的时机的质疑,都合情合理,教授也作了解释(从中暗示了简的性格以及她的生活环境),对话紧凑,没有多余的一个字,一方更多地表现事业心,一方更多地表现人情味,整体上表演性很强,可以不用改编,直接以其为脚本拍成电视剧。“杨枝甘露”是港式甜品,不但与下文太太的话呼应,也符合欧阳太太的身份、经历、教养(上文交代:欧阳太太是绍兴人,到了香港三十多年,早就烹得一手好粤菜)。
有一次,“我”回忆小时候,父亲带他去看修鞋的董师傅,董师傅留饭,发生了一段对话:
这时候,看见有人走进来,是刚才的那个大婶,手里端了个钵,说,董师傅,家里来客了吧,我肚肺汤做多了,给你端了一钵来。
老董谢过了她。大婶说,留客吃饭,好事,缺什么跟我说。临走又转过头来,说,你胃不好,少喝点酒啊。
看她走远了,父亲说,这里的邻居不错,像一家子人。
老董说,风里雨里,也都几十年了。
之所以说“刚才的那个大婶”,是父亲第一次来寻访董师傅的家,董住得很偏,有一段问路的插曲,被问的正是大婶。那个肥胖的大婶正在冲洗一副猪肺,停下来向父亲指路。后面就有大婶端了一钵肚肺汤来“应急”。这里面也有丰富的内涵。固然如父亲所说,邻居间互相友好,同时也反映了邻居对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的老董家境的捉襟见肘了如指掌。这段对话中,大婶的热情对白,恰好对比了老董的沉默寡言(和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经历有关)。“风里雨里,也都几十年了”,响应了父亲的议论,也蕴含了丰富的内涵,暗示了老董也包括胖大婶这些底层人物几十年的艰辛。看她走远了,父亲才发言,既是当面不便以陌生人身份发表点评,也反衬了老董在此需要对胖大婶的热情帮助作出回应的时候缺少必要的应答之辞,父亲以应景也是出于内心的感言来打破沉默的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