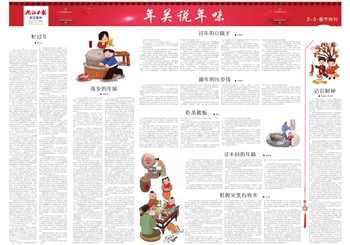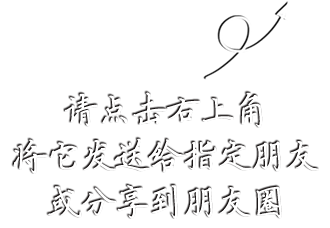■ 邱益莲
有人说:“人生难忘三件事:童年、故乡和初恋”,当初青涩的我不以为然,而今历尽万水千山,尝尽人间百态,才觉此言得之。
行走于江湖,远离着故土的游子,当流光渐行渐远,诸多人事皆已沧桑时,心底时常泛起的是对故乡、对童年的种种怀想。在这无尽的美好怀想中,最让我回味不已的是故乡的年味。
我的故乡在赣北的一个小村庄。村子不大,四面是山,大约住着几十户人家,一条小河从村中穿过,弯弯曲曲,一直流向远方。可小村庄的年味,在记忆中却一直像陈年佳酿,醇厚、纯正,让人回味无穷。临近农历年的个把月,全村家家户户都很忙碌,家家要准备杀过年猪,打过年豆腐,炒过年果子,洗过年衣被……
在僻远的乡下,平时几个月难得闻到肉味,杀过年猪,不仅是全家的一件大事,也是全村的大事。杀过年猪时,屠户请进来后,邻里中会有力壮的男子主动来帮忙,三五个人将一头活生生的猪捉住摁在台子上,协助屠户将猪杀死。杀猪当天,主家会将猪身上每个部位的东西都煮一点,猪肉、猪血、猪肝、猪肺、猪肠,用一口能装一大担水的大锅煮一锅,先是犒劳屠户和帮手,以及家里守望的孩子。接着是用大汤碗给邻里每家送一碗,有汤有肉有猪杂,香喷喷的,热腾腾的。接受的人家道谢后,也会让小孩趁热吃。一家杀猪,家家吃肉,这真是全村人的幸福。主家还要指点屠户按肥瘦搭配,这切两斤,那切三斤的,都用干稻草绑好,然后就给亲戚挨家送去,这叫送年礼。过年猪一杀,热闹的年味就开始在村子里飘香起来。
打过年豆腐,对我们孩子而言,也是一大期盼的乐事。我们参与豆腐的全程制作,也在制作的过程中最先品尝,真是趣味无穷。十来岁的哥哥和母亲一起拉磨,浸胀的黄豆一勺一勺舀进石磨里,出来的是白花花的豆汁,当所有的黄豆都变成汁液后,就倒进灶上的大锅煮,技术活和力气活有母亲带着哥哥做,我则负责坐灶下烧火。这烧火有讲究,先是武火,一口气将豆浆烧开,但是烧开后就得温火,不能太急,火太急豆浆就会溢出来。更重要的是,这过年豆腐是发财豆腐,打得好意味着来年会发财,弄不好就没有好彩头。所以,当豆浆烧开时,烧火的人要心领意会将火弄小点,悄悄减掉几块木柴,但不能直接说“减柴、退柴”之类,因为这与“减财、退财”谐音,这是谁家都非常忌讳的事。打豆腐之前,家家大人都会叮嘱小孩不要乱说话,最好是别说话。记得有一次,当豆浆的泡沫从大锅里鼓起时,我脱口而出问母亲:“现在减柴吗?”母亲对我眼睛一瞪,无可奈何地说:“把火搞小点。”这时我意识到说错话了。
当豆浆在熬煮的过程中,锅面上起一层层豆油皮,母亲会用一根根比筷子略长略粗的小竹棍挑起来晾着,这就是我们自制的腐竹。大人知道我们小孩嘴馋,通常会给我们每人一块豆油皮,热热的吃下,嫩滑油润,喉咙半天还留着清香微甜的味道。
打过年豆腐在村里也算是件大事,邻里经验丰富的长辈会主动来帮忙指导,孩子们围着凑热闹。大人们边干活边聊天,有关打豆腐的趣事一个接一个,整个厨房都是热火朝天的景象。
炒过年果子,主要是炒自家晒的红薯片和打爆米花。每近年关,外地人会挑着爆米机在村里叫喊。长年靠红薯丝充饥的农家这时都会很慷慨地拿几升好米来做爆米花。当爆米机“砰”的一声响,一缕青烟之后,送来丝丝甜香,黑黑的大布袋里像变魔术似的,将那些细细的米粒全变成了白花花的大大肥肥的爆米花了。趁热抓一大把放进口里,米花在嘴里慢慢融化时,带着糖精的甜味,这是一种幸福的味儿。我们家每年都要炸两麻袋爆米花,还要炒一大袋红薯片。除了家里待客,主要是用来三十晚上发给接果子的小孩子。
到了年三十,年味浓得像凝固的蜜糖,可以用筷子挑起来似的。这一天,大人、小孩都忙得不亦乐乎。清晨母亲杀好鸡,将整只鸡用铁炉罐装着挂在火炉的提壶钩上炖,灶上的大锅在炖大块的腊肉、猪脚,母亲站在灶边忙着做肉臊子和糯米果。所有食品全是大鱼大肉,做熟后不切。整只鸡,大块的肉,整条的鱼,分别用大碗装好,臊子、米果、米饭也都用小碗装好放进菜篮,然后放上香、纸、爆竹。十来岁的哥哥提着祭品带着我们到祖父、父亲等先人的坟前祭拜,在坟前先放爆竹,再上香,摆祭品,烧纸,请先人享用。祭祀完成后将一菜篮的祭品全部提回家,再祭拜天地。这些祭祀活动叫做敬神。敬完神,母亲开始将整只鸡切成一块块的,再放到汤里加热。猪肉切成片小炒,还有热腾腾的臊子、米果端上桌,鸡、鱼、肉几大盘摆满一桌,哥哥把他写的对联往大门两边一贴,在门檐上一边吊一个自制的大红灯笼,里面点着蜡烛,爆竹一放,然后就一家人围着八仙桌正式吃年饭了。每家的程序都差不多,庄重的仪式,浓浓的情思,一家人团坐在一起,吃着一年来最美好的饭菜,整个屋子都是暖融融的。
“三十晚上的火,元宵晚上的灯。”三十晚上每家的火炉都会烧着一个很大很大的柴兜,这个大树桩是经过一年的谋划、寻找,甚至是从遥远的深山老林挖回来的。一个柴兜占据了整个火炉,烧时不能用火钳在柴兜上面敲,大人说如果敲了三十晚上的柴兜,家里养的猪就喜欢将猪食盆子打翻。每家的火炉烧得很旺,意味着家旺人旺财旺好发旺。
除夕夜接果子是过年的高潮。天一黑,孩子们每人背个布包,手里提着个老早就准备好的糊着红红绿绿彩纸的灯笼,高呼小叫,成群结队邀着一起挨家挨户去接果子拜年。每个队伍上十个小孩,每到一家,就按辈分喊“娘娘(婶婶),崽姑娌向你拜年,薯片果子先上前”。主妇也会满脸笑容祝福我们,并给我们每人一盘爆米花夹杂炒红薯片。村子的田埂上、小路上,一群群提着彩色灯笼的孩子在游动,田野上恍如游动着一条条彩色的长龙,欢声笑语激荡着恬静的山村,年的气氛被孩子们推向了高潮。游完了整个村子,我们就各自回到自己的家里。这时,又开始给神台上的祖先牌位上祭品,然后放爆竹吃团圆饭。年,就在这欢天喜地的吃喝中行进着……
团年后,就围着大火炉守岁。在充满爆竹硝烟幽香的夜里,母亲一边做着隔年饭,一边给我们讲古。隔年饭意味着年年有余。正月初一是不能动菜刀的,老少都玩,意味着一年轻松。
正月初一,新年开始,十里八乡的玩狮灯、舞龙灯、戏花灯、唱大戏的农民开始一显身手了。平时比较沉寂的山村,从早到晚,锣鼓喧天,一波一波的登场,恶作剧的人往舞龙舞狮的队伍里扔大褂的爆竹,舞的人更加卖劲,这样的热闹要持续到元宵夜。
岁月如流,儿时趣事再也无法重现,村里的青壮年大多迁徙或外出打工了,留在村子里的,也就稀稀落落的几户人家。过年时还有谁去接果子?家家一个小孩,金贵得像宝玉,娇惯得白天也不会随意出门,更别谈晚上去别人家拜年。许多的年俗,在小村里也早已废弃。老一辈的人很多作古了,没有了爆米花时发出的“砰”的爆裂声,没有了夜晚邻里围炉而坐讲古的谈笑声,没有了孩子们呼朋引伴出门拜年接果子的欢笑声,过年的村子也是安安静静。
离开故乡几十年了,母亲早年走了,曾经帮着母亲做年饭,晚上带我们出门拜年接果子的兄长也在五年前往生了,年节的餐桌上佳肴堆成山,可年味不再像儿时那么浓郁,那么让我回味无穷。“人生难忘三件事,童年、故乡和初恋。”故乡曾经浓浓的年味,却在我脑海里经久弥深。是啊,人是只风筝,无论飞多高多远,根的一端总系在故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