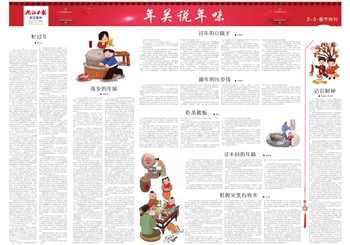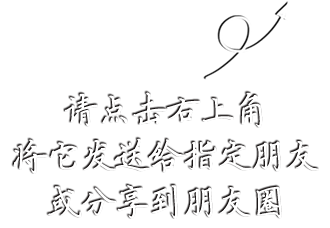■ 钟新强
在武宁,年货是必须有豆腐子。
腊月二十四,琴子家开始打豆腐,过豆腐子了。
琴子嫁到婆家二十年,年年和婆婆一起打豆腐,过豆腐子。在这个传统节目里,婆婆唱主角,琴子打下手,婆媳两人一直合作得很好。
如今做豆腐,很少用手推石磨磨豆子了,家里有磨浆机。按钮一启动,豆子就变成浆水流出来。省事。
大清早,婆媳二人就在厨房里忙开了。婆婆脱去棉袄,只穿棉背心和线衣,脚上是一双蓝色雨靴。琴子身穿薄棉袄套了围裙,脚下是红色雨靴。公公坐在炉灶前,默默地烧火,抽烟。火要烧得好,烧火的是师傅。
一只敞口收腹的大木桶,是打豆腐专用的。桶里侧蒙了一块白色过滤布。桶沿外面,翻套着一圈过滤布。磨好的豆浆,就包在这块白色大布里,安静地躺在木桶中。
开始滤浆了。烧好的一大锅开水,派上用场。婆婆指挥琴子,将开水一盆一盆地往大木桶里倒。沸腾的开水倒入桶中,雪白的泡沫翻涌出来。热气腾腾中,婆婆用锅铲不停地顺时针搅动桶里的豆浆。
琴子将表面那层泡沫捞起来,不要。然后,婆婆撸起袖子,抓住滤布四角,提将起来,豆浆就流在桶里。滤布圆鼓鼓的,里面是豆腐渣和豆浆。现在,需要把二者分离出来。婆婆提起滤布,吩咐琴子将一块井字型的木架平搁在木桶上,悬空的。她叮嘱琴子不要放错了,分清楚木架的正反面。
婆媳二人合力将圆鼓鼓的滤布包袱放在了木架上。豆浆从包袱中奔流出来,流进桶里。七十多岁的婆婆身材瘦小,臂力却不小。只见她不停地用力挤着,滤布的包袱就越来越小。豆腐渣里几乎没有了豆浆。滤出的豆浆全部倒入锅中再次煮沸,然后分别装进了几只小桶里。
现在,到了关键的一步“冲浆”。在这一步,就要放石膏粉了。放多少合适呢?做豆腐论板算,一板豆腐又叫“一汪豆腐”,一般用黄豆十斤左右。婆婆拿了一个喝茶用的纸杯,量了一杯半石膏粉。一板豆腐,就放这么多。这个比例,琴子也知道。二十年来,都是婆婆亲自放石膏粉,亲自冲浆,没让琴子单独试过一次。豆浆遇上石膏粉,发生奇妙的变化,豆腐花出现了。这魔术般的一幕,琴子总想自己试一回。婆婆没松口,琴子就不好多说什么。
将石膏粉用冷水冲泡,倒入大木桶中搅匀后,婆婆说,要倒豆浆了。一声令下,琴子提一桶往木桶里倒,婆婆提一桶往里面倒,公公也过来了,帮忙提起一桶往里面倒。这气氛,有点紧张。
不一会儿,桶里的豆浆就凝结成了豆腐花。豆腐分老豆腐和嫩豆腐两种。老豆腐吃起来有嚼头,嫩豆腐滑嫩。在做豆腐冲浆时,石膏粉多一点,豆腐就老一点,反之则嫩。
琴子家这次做的豆腐主要是为了过豆腐子,所以在豆腐花出现后,还得加了一道工序,那就是要不断搅拌豆腐花。一边搅拌,一边加冷水。据说,这样搅拌后,过的豆腐子里面容易发泡,多蜂窝眼。
搅拌完后,该上豆腐架了。正方形的木架,下有一块底板,板上八八六十四个小方格。豆腐花被包在滤布里,放进豆腐架。架子上面,盖木板。板上,压一块不大不小的石头。
豆腐架四角有口子,豆腐水从中流出来。琴子蹲着,用那温热的豆腐水洗熏黑的烟笋和腊肉。
几分钟后,婆婆拿掉了压在上面的石头,提走木板,揭开滤布,方方正正的一大块豆腐出现了。琴子拿着菜刀,看准了豆腐上印着的小方块格子,横一刀,竖一刀,将豆腐切成小方块。
吃罢午饭,琴子就开始过豆腐子了。烧好一锅水,将切成小正方体的豆腐块倒进水里。豆腐块在水里翻了几个滚后,马上捞起来,再倒进旁边的油锅里过。
油是自己榨的菜籽油,烧热后,香气撩人。琴子以前不知道,锅里倒多了油,将豆腐块放进去后,热油四溅,满灶流窜。后来懂了,锅里只能要三分之一的油。豆腐块在油锅里沉浮翻滚,不一会儿就圆鼓起来,成了豆腐子。一个个色泽金黄,外皮光滑,香气诱人。过豆腐子是很快的,之前花费那么多时间打豆腐,都是必要的准备工作啊。
过好的豆腐子,放进了箩筐里。再到太阳底下晒几天,可存放很久。豆腐子的吃法很多。既可作蒸、炒、炖之主菜,又可做多种肉食的配料,是荤宴素席兼用的佳品。豆腐子炖腊肉,是过年的一道好菜,很适宜下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