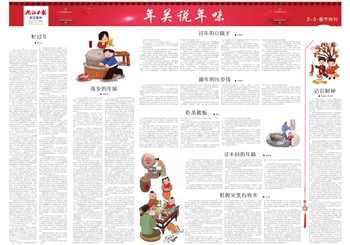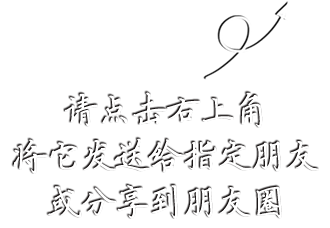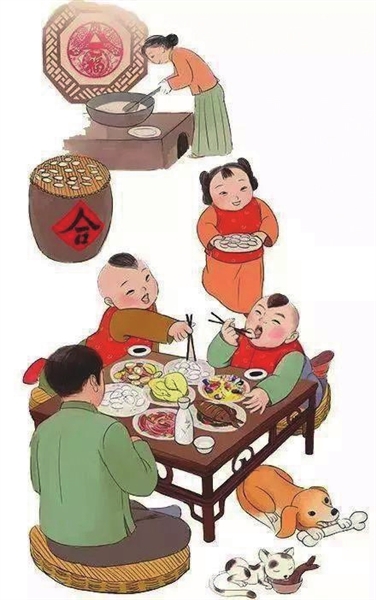
■ 李 琦
“大红灯笼高高挂”挂上红灯笼,春节味更浓。行走在街道,只要留心,就可以看到县城主干道两旁的每根灯杆上都挂起了红灯笼。美丽花形的“欢度佳节”字样里,镶嵌着“公正、爱国、敬业、民主……”等字语,彰显出年的文化和文明,象征着团圆和火红。
无论是晴是雨,白天城市的哪条街上,几乎都是车连着车。少了鞭炮的噪声和烟尘污染,城市的年有了别样的宁静祥和。行人如织,大人带着小孩,步履儿行得快。年,它也长了脚,穿上了红色的、黄色的、紫色的衣服……穿越大江南北、大街小巷,红红火火地来了。
“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迎小年;二十五,做豆腐……”自从我成家后来到县城,每到过年,商场、菜市场、超市都是满满置办年货的人。而最令我怀念的年,是与父母一起过的那些团圆年。
父母在世时,他们俩人年前都忙,张罗着家里是不是少了点什么?从过小年开始,就盼着他们的儿女全家都过来。父亲过世后,母亲照样,就像父亲还在世,一个人做着两个人的事。背着个小包去街上买这买那,一个人独来独往。
时光过隙,想想童年时的年味,盛满了欢乐。小时候,我们家住在山脚下。我十岁时就会去后山上捡柴捆好。回到家里,烧饭的时候,喜欢坐到灶门口去烧火。灶里的火烧熄了,用父亲做的竹子吹火筒吹底下红亮的“火中”,火又呼啦呼啦着了起来。灶里“呼呼呼……”的时候,母亲说那是火在笑,还说,火笑是有客人要来。逢年过节,人情来往,正常不过。倘在平时,灶里的火要是笑,家里果真会来客人,好灵验。我小时候喜欢坐在灶门口烧火,最喜欢听那火笑的声音。听到火笑,我对母亲说,火又在笑哈。母亲说,家里可能要来客人了。
过小年前,父母就把他们种的花生、南瓜子、葵花籽、蚕豆、婉豆、薯片等炒好了。母亲把干净的细沙放锅里炒烫,再把这些零食倒进沙里炒,炒得变了色,闻到香味就盛起来放进筛子里,把沙筛出来。那沙冷后装在小坛子里,下次再炒花生之类的零食。把炒熟了的那些再依次倒在准备好的木器里冷却,冷却过后,再装在瓷器坛里面。糖糕也是自己切,先把芝麻炒熟,再把“打糖”(麦芽糖)炒软,放些糯米做的白泡爆米,和匀后盛放在竹制的圆形播篮里。我看到母亲用两个手把它们揉紧,再挨刀用力切,就成了又香又甜的正宗本地芝麻糖了。在炒制这些熟品时,控制火候很重要。开始下锅炒时,火势要旺,灶膛烧亮。干柴火烧得“呼啦啦”地笑;果子在大锅里“噼里啪啦”地爆跳;慢慢地,火可以边烧边小。火钳在我的手中时合时张,童年的快乐与柴火相伴。
除了这些零食,餐桌上大部分也是自己家里出的。那时候,自家吃不到的红薯、南瓜、薯藤、菜脚、萝卜菜、萝卜等等,用来养猪。吃得不够时,还要去外面打猪草添猪的口粮,纯粹是原生态的猪。有一年,大人们都去山上做事,小孩子不知怎么就玩起了火,点着了里面有猪栏和粪窖的芭葇蓬。等大人们下山,发现蓬子全部烧光了,可怜的猪就任那场火肆虐,全被烧焦。那年,就没有年猪供我们过年了。
那年代,养猪的人家留一头过年,有多余的就换钱,买新衣服或贴补家用。每天剁猪食、煮猪食,猪吃得欢,睡得安。到了过年,就在立春前消猪。母亲一般在小年前看好日子,烧一大锅水,放好家里木制的大猪盆,再加个楼梯、案板什么的,屠夫一来,便可以“消猪”了。消猪的时候,家里很热闹,父母忙碌的身影里,写满了喜悦,脸上洋溢着笑意。过年把猪头叫作“猪神福”。“猪神福”用烟熏了以后,洗净放大锅里煮熟,再分开切,那“砧板香”的味道至今还历久弥新。“二十七杀鸡”,有猪有鸡,年年有余。
如今,城乡的超市里,到了过年,比平时的人更多,都要排长长的队。我的女儿放假回家,除了网购,有时也免不了去超市逛。之后呢,肯定是大包、小包的零食提回家。有时女儿说:“妈,你来吃……”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对那些零食提不起兴趣?而当年,我们吃父母亲手炒制的零食就那么香。现在的孩子,很难吃到我们的父母为我们曾做过的那些年货原生态的味道。那味道才是最本真、最纯香的味道。我常常回味着那柴火灶里火笑的情景,那些柴火锅里食品的原汁原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