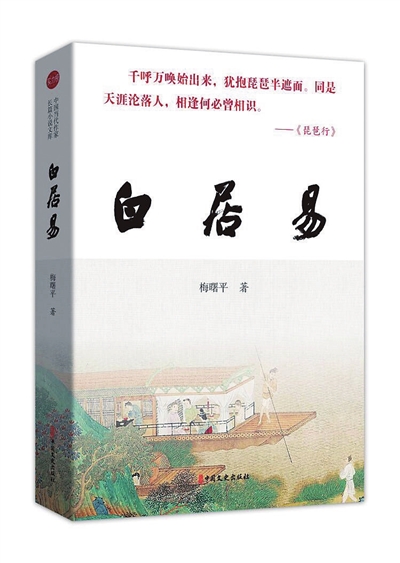
■ 陈杰敏
浔阳的冬天总是一样的。打霜的节气,常常会起雾,灰蒙蒙的一片,像极了唐时江州司马宅附近一片灰色低矮的民居。迟缓的阳光,也是懒懒的,矮矮地打在红土地上,暖色与暖色这么一映照,顿然便有了些许的冬日之暄。这日,在书房稍稍待得久了点,推门出来,蓦然发现,四下里已然灯火阑珊。不由得漫步到浔阳江畔,听那浪花一声声漫溢过来,一声声漫溢开去,脑子里回旋的依然是日前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白居易》(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演绎的风雨人生。面对这一江之水,我禁不住思忖:一千多年前,也是下霜的时节,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乘坐的驿舟,约莫便是从这儿拢岸的吧?
抬眼看了看身后的九江,车流像蜗牛一样在眼前爬行,声音流水一般,隐隐约约的。只有灯光变换闪烁,使得那高高低低的楼房炫目叠彩。这城市的外在景观迅速地趋同,日渐失去特定的文化色彩。守望精神家园,唤醒历史文化,组织作家编写九江的圣哲鸿儒、文宗科魁、良史名士,应该是应时当令。积石如立,列松如翠,在现代狂潮之外,聆听九江独树一帜的历史的声音,也许能够在表面的喧哗悸动下,叫人看起来,这地域不那么单薄与浮华。基于此,九江本土作家梅曙平以白居易为引线,串起浔阳的地域风貌和文化渊源,把这块热土的人文历史描绘得淋漓尽致,应当是以正史之笔,为地方立传的文化尝试与负载。
记得《白居易》中描叙大诗人初踏江州的情形,每根头发都在痛:“黄昏时分,下起了蒙蒙细雨,沾衣欲湿,飘在层层波浪上,袅起一缕一缕的水烟。白居易眯缝着双眼朝长江南岸望过去,三四里的光景,有一对华表高高矗立在江岸边,似张举的双臂,怀抱东来西往的过客。白居易脸上露出了一丝苦笑,没料到第一眼看江州,印象里竟然是一对‘谤木’,真个充满了讽刺。博古通今的白居易自然晓得华表最早称作谤木,相传远古尧帝立木牌于通衢要塞,供臣民书写谏言,针砭时弊。后来,逐步演变成交通路口的一种标志。眼下,自己可不是因为‘针砭时弊’,才贬谪到凄风苦雨的江州!”
小说《白居易》从大唐宰相武元衡遇刺,白居易以道奋直,越职言事,为宵小构陷贬谪到江州写起,以诗意的笔调集中描述了这位淹博大儒在江州三年零五个月的蹉跎人生。作家秉承大处不虚的创作原则,塑造了一个忠国事、劳民事、身先躬行、重情重义、怜老爱子、钟爱自然的“诗魔”形象。作家挥毫落纸之间,也便时间重获,进入到大唐各种时态和处境,在温煦降临的一阵灰色视线中,鸟瞰视点,故事重现。纵观作品的纵向脉络,大量运用了倒叙、插叙、梦呓、旁白等手法,将白居易担任翰林学士与左拾遗期间,敢在天子面前争安危的识见与胸怀巧妙穿插进线性叙述的经纬,鲜明地刻画出社稷之才优异于清流名士的雄浑气魄与艰难努力。小说以大开大合的故事情节,透彻展开了白居易从政生涯的抱负和身边挚友的成功与失败,以及治乱之间文化支撑力的盛衰。以此为基础,作品还极为辽阔地叙述了平定淮西的庙堂谋划与李愬雪夜入蔡州等重大的历史场景,由此,文本的艺术重心便有了大唐文化演变的高度,从而更为深入地开掘和探究了白居易贬谪背后的心路历程与精神底蕴。小说又以襄阳偶遇作由头,巧借白居易的追忆,临水照花地描画出他与初恋情人湘灵的悲苦情缘。大时代与小儿女相互杂糅,所形成的文字妩媚庄重,美丽而苍凉。作家有本事把乱世血泪与儿女情长一股脑儿贯串起来,仿佛青瓷烘衬在火焰里,仿佛同时应和在铜号与竹笛交响回流的旋律之内,也便产生了那些令人震惊的美和力的段落。其中有关于爱情的喜怒哀乐,有关于友情的生死别离,有关于命运的阴晴圆缺,更有关于信念的执着坚守,当众多诗意的词句与丰富的情感排列在一起,便各自都熠熠生辉。作家对白居易的剀切与剖析是多层次、多侧面的,值得注意的是,其笔下没有犬儒的玲珑剔透,没有中庸的骑墙乡愿,文本方得“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求真、求雅之于作者,正如昨夜的宿酲,前宵的余韵,偶尔兜上心来,便给作品平添了意想不到的层次感和穿透力。正是亏得这一脉的天真,无论是对大儒白居易的廊庙之音还是江湖心路的描写,无不流丽天然,没有落入“一说便俗”的通病。
再絮叨小说的横向关联。作家极为生动地刻画出湘灵、白妻杨氏、元稹、裴度、李愬、崔能、白行简、白幼文、刘十九、元集虚、刘珂、王涯等近百位可圈可点的人物形象,有的才华卓绝、抱负不凡;有的雄才大略,杀伐果断;有的重情重义,温婉风流;有的巧于仕宦,号令无节:诸多人物有重有轻,一一镶嵌在波澜起伏的削藩中兴的时代背景中,灿烂、完整而生动。作家还以绰有余妍的笔力,极为广泛地评述了种种文化掌故、文化史实和中唐士子的逸闻趣事,铺展出浓郁的超越具体历史生活场景的文化氛围。进而,小说对官腐民劣、藩镇割据的中唐乱世,对白居易既忧国怜民又对宪宗皇帝图报私恩的历史和文化的必然性,对他“文章合为时而著”的艺术观点及其构建园林的先驱眼光,着力展开了内蕴深厚的表述,从中深刻揭示出人物种种社会与人生抉择的人性、人情和文化依据。小说以白居易人生观的蜕变以及经典诗词为全书的思维焦点与框架,这本身就体现出一种拨开政治文化与世俗道德的迷雾,再现历史人物本相的审美价值取向。通过这样的艺术途径,小说艺术地达成了还原大唐文化脉络的创作意图。
《白居易》的思想内核,则是以认同与反思相结合的态度,讴歌和重审了作为儒家文化正统的立功、立言的文化人格在民族大局中的历史形态及其悲欣交集的命运。小说四十万字的巨大篇幅,用钦敬、仰慕的笔调,鲜活地刻画出白居易为国挺身而出、为民敢于直谏的为官气魄与以诗代谏的才干。对白居易在《与元九书》里倡导的新乐府运动以及《庐山草堂记》中标杆的园林美学,作家更是浓墨重彩地加以渲染。对白居易留下的《卖炭翁》《观刈麦》《长恨歌》《琵琶行》等传世名篇,作家无不以义理、辞章、考据融为一体的学者姿态,穷究诗词背景的来龙去脉,以凝聚大诗人丰厚人生与文化沧桑的沉雄力道,使之成为小说人物贯穿古今的高格气度。
古人曰:人无癖不可交,以其无热情也。《白居易》的作者梅曙平的癖好恰恰很多。他擅长诗歌与散文,爱好国画和摄影,收藏亦有所涉猎,其专业职称是工程师,如此种种,令他的艺术感觉比较细腻灵动,在追求历史视野的行文中,避免了冗长枯燥之弊。在对小说人物世事人生进行理性思考描述的同时,显然还在文本中对传统书画、戏曲、围棋、服饰、官僚体制以及茶酒文化等诸多领域做了别开生面的阐释。《白居易》的文化气度表明,它确实达到了一种真正高品位的美学境界。因为说到底,艺术境界是一种由人性和人生阅历经过漫长时间沉淀而成,作者可贵之处在于,善于将这些积累化作了小说的特定话语形态。
在时间轨迹错综交会中,《白居易》细腻地展示了白居易在江州这片土地上留下的生命印记,也详尽地描绘了九江的山水自然与风土人情。毕竟任何漫无节制的臆想,终归还是要落地生根的。白居易在这一片热土上留下了三百七十首诗文,浩繁的卷帙自此叱咤在匡山浔水间。毕竟白发渔樵江渚上,谣歌反复翻唱的便是那浔阳江上的琵琶和大林寺的桃花,由不得后人随意地质疑抗颉、随心所欲地编排与戏说。
走笔至此,忽然记起作家在《白居易》里,以诗意的语句描述白居易辞别江州时的心境,在此不妨重温一下:“临别惝恍,一桩桩、一件件往事,如那大江东去,何曾稍息?白居易只记得:草堂风月相迎,频回盼睐,便认得琴心先许。但过了烧灯后,都不见踏青挑菜,几回凭双燕。丁宁深意,往来却恨重帘碍;白居易兀自记得:漫揾英雄泪,相离长安远。谢慈悲,坐禅莲台下,没缘法,转眼分离乍。那里讨,烟蓑雨笠单行。一任俺,芒鞋青衫随缘化;白居易怎能忘记:作诗用新笔,满纸怨望,嗟卑叹老。登庾楼,问天罟人,强相愤慰。厮磨领悟,编辑百来篇章,终究成集。与元九书,启迪成手,助其天真;白居易如何忘记:司马宅庐,拙荆在堂。左对孺人,右对稚女。天涯兄弟,晨夕过从。千里不异比邻,两地无殊揽袂,山川虽阻,神明不隔……”
是的,小说《白居易》意欲展现的何曾不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命运之间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