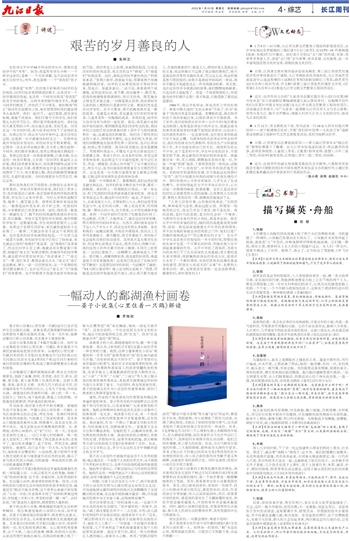■ 朱阿正
在彭泽太平中学66年毕业的学生中,我绝对是同学中的“另类”。因为:我是所有学生中唯一一个转学过来的;是唯一一个非彭泽籍,也不会说彭泽当地方言的学生;另外,我也是唯一一个“劳改犯”的子女。
尽管我是“另类”,但丝毫不影响我与同学的友好相处,同学们也非常照顾我的面子,从来没有一个同学揭我的伤疤,也没有一个同学因我是“劳改犯”的孩子而歧视我。从转学来到新环境没多久,我就与同学们熟悉了,并结识了不少朋友。他们称我“阿正”而没有在前面加上姓,现在想想那时我们就显得多么亲热呀。我们一起学习,一起打篮球,甚至违反校规,偷偷下河游泳。我们不像今天的学生,他们有那么大的学习压力。那时是不唯成绩论的。我们这些天真无邪的少年,快乐地生活着,无忧无虑。仅仅在这一年半的时间,我与很多同学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我记忆中,我从未与同学争吵过,甚至没有红过脸,这是我一生中最愉快的时光之一。在我毕业离开学校回乡劳动后,有的同学还专程来看我。我记得有一次去彭泽县城办事,在大街上偶尔碰到一个同学,我们都非常激动,竟然忘情地相互拥抱在一起。更难忘的是有一次我卷着裤腿,打着赤脚,在山边的一块水田犁地,正好我一位同学扛着扁担上山砍柴,我们虽然都非常高兴,而他看到曾经活泼少年的我如今如此不堪,我看到他也许是生活的重担使他憔悴了不少,双方都很心酸,我们的眼睛里都噙着泪花,互道珍重话别。当时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那时虽然我们学习很轻松,但物质生活条件是非常差的。学校没有像样的食堂,我们自己带米上学,吃的饭是自己淘米,装在饭钵里放到学校的蒸笼里蒸,学生自己从家中带菜。当时大多带的是酸豆角、腌萝卜、霉豆腐之类。我带的菜相对来说比较好,一般都是油炸花生米、炒干虾之类。吃饭的时候,大家都把自己的菜拿出来一起吃,我的菜一般是只一顿就吃光了,剩下的时间我就到其他同学处吃菜,其乐融融。学校不是无偿给学生烧饭,每学期要给学校交一定数量的柴,学生则利用星期天上山砍柴。如果这个星期天没回家,家长就知道他孩子去砍柴了,一般第二天就会给孩子送这个星期的菜来。也许是有的同学家离得比较远,一个大劳力送一趟菜不划算,有的同学在家中已经订了娃娃亲,家长就会让他的“准媳妇”来送菜。这“准媳妇”送菜来了,而这位同学正在上课,她就会站在教室窗口张望,而她的“准丈夫”如果没看到,但被另外的同学看到,就会轻声对那位同学说:“你老婆来了。”“准丈夫”一看,连忙举手,教师会意点点头。“准丈夫”连忙走出教室,俩人一前一后回到宿舍,这一个星期的吃菜问题也解决了,也许还可以让“准丈夫”与“准媳妇”培养感情。这个时候我才知道当地有对娃娃亲的习俗。我自然也上山砍柴,家离得比较远,父母也没有时间给我送菜,我又没有这个“艳福”,有“准媳妇”给我送菜。这时,离校近的同学就对我说:“到我家拿菜。”星期六放学,我拿起书包,里面装两个玻璃瓶就和他回家。同学的父母看见他孩子带同学回家,很高兴。知道来意后,二话不说,拿着我两个玻璃瓶,走到泡菜坛边,弯下腰,抓出腌萝卜、酸豆角,把我的玻璃瓶装得满满的,然后交给我。既无施舍之情也无吝啬之意,一切都是那么自然,我在我同学父亲的脸上看到的只是慈祥的父爱。晚饭自然也是在同学家吃。在今天看来,那天的晚饭绝对是一般的饭菜。也就是大米饭,菜也就是当时农村的家常菜:几盘青菜和一些腌制的咸菜。奇怪的是,同学的父母并没有与我们一起吃饭。饭后,我无意中走到同学家的厨房,看到锅里是我们没有吃完的饭,我同学的父母把已经切碎煮熟的萝卜菜叶子与那些剩饭和在一起:这就是他们的晚饭。他们为了招待我们这些小客人,即使饭不够吃,也让我们吃大米饭,而他们却默默地在厨房里吃萝卜菜拌饭,也不让我知道,怕我心里不舒服。我当时深为感动,甚至是震撼了。可惜那时我还小,不懂也不会用言辞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参加工作后,生活条件好转,享受过很多美味佳肴,也出席过不少丰盛的筵席,至今记忆全无,可这一顿晚饭,在我心田中留下了永不磨灭的记忆,终生不忘,连当时厨房的情景直至今天都历历在目。这也是我一生中最丰盛最有意义最难忘的晚餐,它胜过所有的我所品尝的美味佳肴。
转眼一个学期结束了。暑假期间,我们这些好朋友就互相走访。同学们的家分散在各个村落,都有一段路程。我们带上一些简陋的日用品,一家一家走访,到了吃饭的时间走到谁家就在谁家吃饭。我也没有考虑这么多,就这样与同学们一起走,开始时三二人,后来变成五六人,又增加到七八人,我们这些无忧无虑少年,走在田间小路,一路上有说有笑,叽叽喳喳,像一群快乐的小鸟,至今想来,心中仍充满着幸福感。来到一个同学家时已经到了吃晚饭的时间了。吃过晚饭,天黑了,不能再走了,就在这位同学家睡,明天再到另外的同学家去。大热天,那时谁家也容不下这七八个半大小子,再说也没有那么多蚊帐。家长和我们一起搬出板凳、木板在外面搭床,然后点上艾草用来熏蚊子。露天睡觉,用艾草熏蚊子,有时蚊子也会趁机向我们发动进攻。虽然我不是大都市生长的,但这种生活我还不适应,我有点担心我睡不好。我们这些小伙伴在露天的床上躺着,头顶天上的星星,一边拍打着蚊子,一边聊聊天,渐渐地进入了梦乡。那天晚上,我睡得特别香,我也感到好奇怪,难道是蚊子没有来骚扰我?还是我已经适应了在蚊虫叮咬下睡觉?还是那位同学的妈妈一句话解开了谜底:“XX与阿正真好呀!晚上还为阿正赶蚊子。”我想,可能是这位同学知道我是外地人,担心我不服当地水土,在他的潜意识中,他是主人,招待好客人是他应尽的义务,他这样做只不过做了他应做的事而已,绝不是商品经济等价交换的关系,可以这么说:他这样做是绝不图回报的,如果不是我同学妈妈的一席话,我至今都还不知道有这么一件令我感动的事。我又想,也许还有很多令我感动的故事,他们默默地奉献着,只是没有人提起罢了。我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但我能为同学们做什么呢?我不知道,只能是除了感动还是感动。
1966年,我从学校毕业,再也没有上学的权利了。席卷中国大地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作为“狗崽子”的我自然是在劫难逃。更糟糕的是,我在转学时由于我的家庭出身,以致彭泽县中不接收我。为了求学,我只好转到乡村中学—太平中学(现在看来也没转错),如果是彭泽县中的毕业生,我就会成为知青而获得知青的待遇下放到彭泽农村,以彭泽人民的善良和淳朴,一定会善待我,也许我生命的轨迹不至于如此之糟。与我类似的在彭泽县中毕业的学生,他们有的成为当代课教师,有的在生产大队搞宣传工作,多少也能发挥自己的专长。而我所在的太平中学,由于是农村中学,学生毕业统统回乡,不需要安排下放,我也就很自然地回到农场务农。我就像垃圾一样,无人理睬,默默地在农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修理”地球,干着和劳改犯一样的活,活脱脱就是一个“小劳改犯”,中学所学的知识毫无用处。有的同学知道我的处境,至今提起还说我那时“好苦”,语气中流露出对我的同情与对我处境的不平。那时的我内心当然非常痛苦,几乎失去了生活的勇气。但有时想起在太平中学快乐的日子,心中泛起一丝微微的暖意,倍感温馨。也许正是这美好的回忆让我感受到人间的温暖,让我看到人生的希望,看到人类美好的一面,鼓舞我坚强地活下去。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光阴荏苒,种种痛苦与悲伤,都如过眼云烟。即便有一些痛苦的记忆,我也已学会了宽容,而不是仇恨。我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是当时社会的一个缩影。与那些付出生命代价的人相比,我是幸运的。而在太平中学的幸福的回忆,随时间的流逝愈加更加鲜明、深刻。我也深深地感谢太平中学的老师领导,并不因为我的家庭出身把我拒之门外,他们以宽广的胸怀接纳我这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在太平中学生活虽然只有短短的一年半的时间,即便在我的生命中也是一个不算长的时间,但她在我人生中却起着重要的作用。太平中学给了我知识,为我今后的高考打下了扎实深厚的文化基础;更主要的是在求学期间,我接触到彭泽县的劳动人民,使我对人生有了一个新的领悟,对他们优良的品德有着亲身的感受,即使在人性泯灭的“文革”中,也看到人类美好的一面,也使我坚信善良一定会战胜邪恶。谢谢你们,淳朴善良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