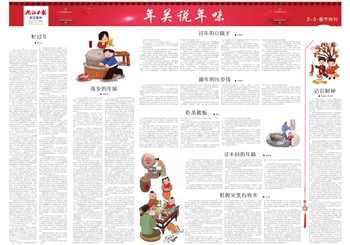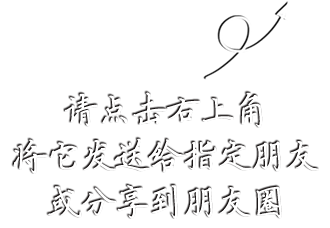■ 景玉川
一
在我小时候只知有过年,不知有“春节”。“春节”是我上中学以后才听说的词语,其实,它也只是在民国时才开始使用。那时在我们小县城,“元旦”人称阳历年,“春节”叫阴历年,阳历年似乎与小孩无关,只有阴历年才是孩子们所盼望的。每当临近阴历年,孩子的心里都充满了温馨,无论他们的家境是贫穷还是富裕。
进了腊月,小城的气氛渐渐变得温暖融和起来。家境稍好的人家,早在立冬后就开始腌制腊鱼腊肉。过了腊月二十,离年越来越近,小学也放了寒假,在此前后大人对孩子的警告常常是:“细伢子莫劣(顽皮),小心打一顿过年。”为了不挨这一顿打,再顽劣的孩子也会有所收敛。小心翼翼等到挨过了腊月二十三,那就万事大吉了,因为过了小年,大人再也不会打小孩。大概由于在过年期间,打骂声与哭喊声会影响过年的喜庆气氛,所以父母对孩子的严惩,一般都在过年前。腊月二十三是打扫卫生,祭拜灶神的日子,灶神北方称灶王爷,我的家乡则称“司明爹”。这一天,不仅卫生要打扫得彻底,大人还会一再嘱咐小孩不要乱说话,因为这天是“司明爹”上天的日子,人们希望他“上天”后在玉皇大帝面前多说这家人的好话。故砌有大灶的人家,会在灶上方烟囱旁贴上寸余宽小小的红对联:“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
腊月二十四是小年,平常人家这天餐桌上并不丰盛,仅有不多的鱼肉而已。不过,让人振奋的在于:一过小年,家家户户女主人们就要忙着炒花生、瓜子、豆子和切糖糕。糖糕用炒米和米糖(家乡叫“打糖”)在大锅里混合,再掺以花生仁、芝麻或桂花,然后趁热切成小薄片。这种糖糕又甜又香又脆,比如今超市里卖的冻米糖好吃多了。家乡人称糖糕会在糕后加一个“得”音,说成“糖糕得”,就像北方话中的“儿”音一样。炒花生切糖糕的这一天,灶膛里炉火熊熊,屋内花生、瓜子、糖糕香气弥漫,孩子们兴奋而活跃,基本上不会离开厨房,偶尔也会去屋外放一两个爆竹。
到了腊月二十六,就开始有人家“还年福”了。小城里每家“还年福”的时间有所不同,分别为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和三十,所以这几天每天下午晚上小城里鞭炮声不断。我至今也不知道“还年福”三字究竟应该如何写?只知道这一天全家人要在一起聚餐和祭祖。至于“还年福”时间的不同,则在于各姓氏家族祖上制定并传下来规矩。听父亲说,我家“还年福”的时间原本在腊月二十九日半夜,也就是除夕日的凌晨,后来不知哪一代大人嫌麻烦,将“还年福”与除夕合二为一。北方民俗很重视“腊八节”,在我的家乡,好像没有这一节日,我只是在长大后从书报上才知晓”腊八节”的。
除夕日这天下午,进城的人都返乡了,各家店铺也陆续关门,街上少有行人,小城恬静而安详,散发着过年的瑞气。入夜,鞭炮声此起彼伏,震响夜空,空气中飘散着好闻的硝烟气息,各家都在吃年夜饭。
我家由于“还年福”与除夕合一,所以大年三十晚上还要祭祖。景姓是小姓,在城里没有祖厅或祠堂,祭祖在家里进行。厅堂上方有一神龛,神龛中摆放有“天地君亲师”的牌位,前有香炉、烛台,神龛两旁写有“金炉不息千年火;玉盏常明万岁灯”的对联。那对联写得好,字也好,所以几十年过去了,我依然不忘。燃烛、焚香、放鞭炮、祭拜之后,一家人便开始吃年夜饭,此时家中在外的人再远也会在饭前赶回来。年夜饭是一年中最丰盛的晚餐,号称“十大碗”,鱼、鸡、笋、粉丝、猪肠、薯粉汤、肉丸……还有我最喜欢吃的红烧肉。星子地瘠民贫,历来来待客的最高礼仪便是“十大碗”,所以除夕年夜饭也是“十大碗”。附带说一句:小时不知“除夕”,只知(大年)三十夜,“除夕”这一词是长大后才知道的;北方除夕夜兴吃水饺,南方好像没有这一习俗。
年夜饭之后,孩子们会到屋外放炮仗,放烟花是有钱人家或十多年之后的事。年饭后孩子们开始向父母长辈要压岁钱,这也是他们最渴望的事情。我家穷,兄弟姐妹多,所以压岁钱很少,一般是伍分、一角,顶多为两角。不过,这些钱都是父母年前就换好了的崭新纸币,所以钱虽少,我们也满心欢喜。“三十夜,侃大话”(家乡方言中,“夜”与“话”押韵;“侃”念作kuang)。意即这一夜可以畅谈志向,甚至能吹点牛。三十夜还要“守岁”,即守到天亮不睡,开初孩子们也都有守岁的雄心壮志,可熬了一阵,一个个忍不住哈欠连天,到了十二点前后,终于撑不住,先后上床睡了。
第二天是正月初一,天刚亮,父亲就打开铺门燃香烛,放鞭炮,这叫“出天方”,大概是乞求新年好运的意思,只是我一直不知道这“方”字究竟该如何写?“除夕”夜祭祖放鞭炮时,大人还会将一块劈柴丢到门外,“柴”与“财”同音,自然也是乞求发财。所以“出天方”时,那块昨夜丢出去的劈柴,会被捡进来。
“出天方”前后,小孩大都醒了,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给长辈拜年,要跪拜。正月初一的早餐在我家好像不太讲究,或面条,或菜饭。饭后则在客厅摆出糖糕瓜子香烟等,准备招待来拜年的客人。早餐后父母会吩咐孩子出去拜年,主要是给左邻右舍的店老板和在城里的亲戚拜年。拜年时,要跪下一条腿或双腿,受拜方的大人会对来访的小客人说:“啊呀呀,快起来,就是一样,天保佑你肯长肯大”(“肯”是“快”的意思),说罢则给小客人糕点。拜年归来,每个孩子的荷包里,都塞满了托(“托”有犒赏的意思)来的糖糕之类的食品,有的还会有几支香烟。所得较多的孩子,自然有几分神气。
初三初四,乡间耍龙灯的队伍便进城了,队伍中还有舞狮、踩龙船和耍蚌壳。男人有时会对张开的蚌壳哈哈大笑,大概蚌壳象征女性吧。正月初八,小城各家店铺开张营业,除了晚上的龙灯,过年的气氛有些淡。那时居民生活水平不高,年前腌制的鱼肉也吃得差不多了,“拜年拜到初七八,坛坛罐罐都洗刮”,普通人家连糖糕薯片之类的食物都吃光了。不过,到正月十二、十三,“年”的气氛又浓起来,到十五日形成最后的高潮。
正月十五是元宵节,这一天小城张灯结彩,每家店铺门前会挂出灯笼,居民午餐或晚餐以吃食汤圆为主。这天晚上每家都灯火通明,每一间屋子,哪怕是小过道,都要点上蜡烛,以求新年前途光明,大吉大利。我们小孩手上则拿着樟树枝或榨树枝,让树叶在蜡烛上烧得噼啪响,嘴里喃喃道:“照什么照胜,一年胜一年……”元宵夜进城的龙灯队伍最多,小城里铳炮震响,锣鼓喧天,火树银花,“一夜鱼龙舞”。有的舞龙队耍龙时会不小心被龙腹中的蜡烛烧了龙身,整个龙队这一天不免有点狼狈。
元宵节过完,春节也就结束了。
“月光爹爹,保护娃娃;娃娃长大,好做买卖;买卖赚钱,犒猪过年” (这里”犒”应念作gao,是杀的意思)。“大人望赚钱,细伢子望过年”……这是我小时熟悉的儿歌,儿歌中都提到赚钱,不知是否与小县城里多是生意人有关?因为我的父亲也是星子县城一位小生意人。所以我关于过年的回忆,也许带有买卖人家的特色。
二
以上所写的过年风俗,在我的记忆中其实也只经历过一两次。因为在这以后,家里家境日难,渐渐社会上物资供应紧张,“左”倾思潮逐年高涨,小城过年传统的喜庆气氛自然大打折扣。
记得1960年春节,正是“大跃进”后的困难时期,大年三十无肉,父亲好不容易从乡下姑姑家搞到了一块肉,那肉不过斤把重,很像是病猪或猪崽肉。但全家人还是欢喜异常。
再后来,就是提倡“过革命化春节”,“年”的气氛更淡。那些年,人们在外面过“除夕”的也不少,我在乡下和矿山就度过了好几个“大年三十”。不过,虽说提倡“革命化”,但作为最重要的传统节日春节,在一般的百姓心中还是不易被“革命化”化掉的:只要有条件,在外当兵做工务农的人,都会尽量赶回家过年,哪怕远在千里;在外过“革命化春节”的人,单位也会组织他们加餐、开晚会,热闹一番。
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传统节日关联着民族情感和民族精神,给人带来心灵的抚慰与温暖。即使在物质异常贫乏的年代,生存异常艰苦的环境,这一天哪怕过得再简单,再朴素,但佳节所负载着的美好愿望和生活理想,仍能给人带来温馨。“告花子也有年节”,“千里之外也要赶回来过年”,这些记述先人习俗的古话,显示着我们民族顽强坚韧的文化传承。
1979年春节,我在广州我的老师家过年,那时打倒“四人帮”不久,老师还是“现行反革命”,他与妻子离异,上有老母下有弱女,生活极其艰难。广州除夕夜兴花市,大年三十夜市民倾家出门去逛花市,我和老师一家也不例外。花市上欢声笑语,观花人熙熙攘攘,街市两旁群花争妍,芬芳飘逸。花价有几元、几十元、数百元,最贵的要上千元。我们买不起,只要了两枝一角钱一枝的银柳。花市归来,将银柳插入小瓶,我也感受到了南国除夕夜满室盎然的春意。
近十几年来传统节日气氛日淡,洋节反倒时兴火爆,尤其是在年轻人中。有人将这一变化归结于物质丰富,生活水平提高,这貌似有理,实则不然。你看《红楼梦》中的贾家,何等富贵,而贾家的春节,过得是何等隆重、排场和喜庆,特别是贾府的除夕夜、正月初一与元宵节。每个国家的百姓对本民族的传统节日,我想都应会感到亲切。
2007年国家将除夕、清明、端午和中秋定为法定假日,实在是明智之举。传承着民族精神与情感的节日,将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欢乐、和谐、温馨与诗意。
愿每一个春节都能给孩子们留下美好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