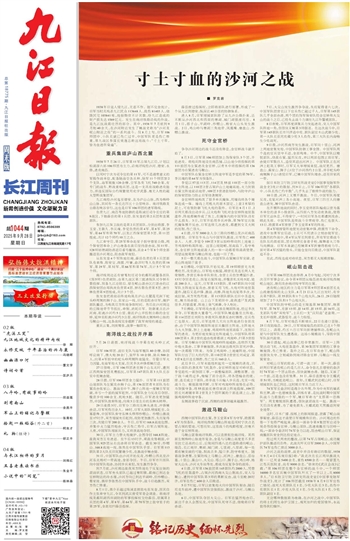■ 罗克岩
1938年日寇入侵九江,无恶不作。据不完全统计,日军当时共残杀九江民众113648人,致伤81403人,烧毁民宅103841栋,抢掠物资不计其数,给九江造成的财产损失达1589亿元。发生在南浔铁路沿线的作战,是九江抗战最壮烈的部分。其中,1938年7月底到9月初40余天,在沙河附近发生了被战史称为“沙河及岷山附近之役”的一系列战斗。仅8月上旬,日军106师团中、小队长就已伤亡过半,中国军队更是伤亡惨重,第九战区参谋长吴逸志称这场战斗:“寸土寸草,皆为血迹所染遍”。
重兵集结庐山西北麓
1938年7月26日,日军第11军占领九江后,计划以松浦淳六郎106师团为主力,沿南浔线经沙河、德安、永修,进攻南昌。
以冈村宁次为司令官的第11军,可不是通常意义的军级作战单位,配备陆海空各兵种,陆军11个师团加2个支队,海军舰艇120余艘,空军各类飞机740余架,有专门的战车、野战重炮兵团,这是一支具有战略进攻能力,并违反国际公约频繁使用化学武器、毫无人性的超大型野战集团军。
九江南经沙河迤至德安,东为庐山山脉,西为株岭山山脉,其间有一条长达四五十公里峡谷。南浔铁路及公路在峡谷穿行,这也是日军106师团的进军路线。
负责九江、南昌等地防御的是陈诚任司令长官的第9战区,下辖薛岳的第1兵团、张发奎的第2兵团和直属部队。
参加九江保卫战的是第2兵团部队,分别由欧震、李玉堂、王敬久、李汉魂、李觉负责的第4军、第8军、第25军、第64军和第70军,以及江西保安团第3团、第11团组成,共计12个师约10万之众。
九江弃守后,第25军奉命赴星子扼守德星公路,两个保安团奉命上庐山准备在敌后坚持游击战,预11师、128师姑塘湖防溃退后番号撤销,其余4个军8个师全部撤退至沙河周边,阻击敌军南犯。
从张发奎4个军阵地往南,薛岳负责的第1兵团部队有黄维、陈安宝、商震、叶肇、俞济时等人负责的第18军、第29军、第32军、第66军和第74军,共计5个军13个师。
南浔线周边还有曾戛初任司令的鄱阳湖警备部队(预5师)负责湖防,由第九战区第三挺进纵队司令钟石磐指挥,预备九江沦陷后,留在岷山游击区打游击的江西保安团由郑执庆负责第4团、钟石磐负责第5团、唐仕林负责第9团组成,共计3个团。
张发奎把最前沿阵地构筑在庐山北麓莲花洞下蛇头岭两侧的狮子山、张家山一线,目的是阻击日军,掩护部队撤退,为构筑后方阵地争取时间。然后在沙河周边的丘陵地带节节抵抗,牵制、消耗日军。防御重点在沙河南,距离沙河约5公里、靠近庐山并控制公路的金官桥,延伸至距离沙河约3公里、南浔铁路北侧株岭山脉的马鞍山一线,这条战线完全截断了敌军南侵的通道。
重兵云集,剑拔弩张,战事一触即发。
南浔线之战拉开序幕
7月26日清晨,南浔线战斗序幕在蛇头岭正式拉开。
日军106师团、波田支队与海军舰队80余艘,协同呼应南下,携大炮20余门、装甲车10余辆、骑兵500余人,向第4军扼守的蛇头岭两侧阵地猛攻。尽管日军火力凶猛,有海军炮火支援,但其多次冲锋都被打退。
27日傍晚,日军106师团进至狮子山东北时,遭到江西两保安团英勇抵抗,日军第147联队第3大队长谷实中佐被击毙。
28日晨,日军106师团全力猛扑。日军第111旅团山地部队为左翼攻击狮子山,第136旅团青木部队为右翼攻击张家山。激战至中午,狮子山阵地一度被日军突破,幸亏一个旅的援军赶到,中国军队全力反攻后夺回,缴获步枪100余支、机枪5挺。随后,日军进攻更加猛烈,中国军队放弃阵地,向南3公里左右的东林头转移。
29日凌晨3时,日军分三路向东林头进攻,冲锋被击退,日军死伤百余人。10时,日军大部队增援赶至,众寡悬殊,中国军队弃守东林头移师纱帽山。纱帽山激战至17时许,双方增援先后赶到,攻防更加激烈,失而复得三次,共毙日军200余人。午后,日军对168.8高地包围,并集中火力猛烈炮击,守兵伤亡殆尽,日军占领阵地。入夜,中国军队增派兵力,又将该高地夺回。
30日,日军主力借火炮掩护,企图夺回168.8阵地,敌我双方互有进退。至午后13时许,乘敌攻势稍弱,中国军队925团从右出击将日军击退。截至30日,纱帽山、168.8高地一线,依然在中国军队手里。日军第113联队第2大队长田尻繁雄少佐,在激战中被击毙。
31日,中国军队由沙河开始反攻,纱帽山西北至沙河东北杨村一带高地,全部夺回。午后,日军市川部队向中国军队炮击,协同步兵来犯,发生激烈争夺。
到7月底,沙河周边敌我双方阵地处于反复拉锯的混战状态,日军先头部队已越过赛阳镇,最南已到达金官桥附近的冷水堰,沙河方向已到达平湖岭,但纱帽山、曹家垅、崩岸李依然在中国军队手中,战斗日趋激烈,双方伤亡惨重。
8月1日,蒋介石越过陈诚直接致电张发奎,因其自作主张弃守九江,令其到武汉接受军委会调查。将南浔线及鄱阳湖西岸湖防的军事指挥权交给薛岳,原属第2兵团的第4军、第8军、第64军、第70军加上驻守星子的第25军,全部划归薛岳指挥。
薛岳接过指挥权,立即将部队进行部署,形成了一个从九江到德安,纵深近40公里的防御体系。
进入8月,日军增援部队除了从九沙公路扑来,还不断从沙河西北和西面的赛湖、城门湖强渡而至。8月1日,搭子山、平湖岭、纱帽山、杨家大山头发生激战。2日,鸡公岭与赛湖三角地带、凤凰嘴、磨盘山、纱帽山激战。
死守金官桥
争夺沙河周边的战斗还没有停息,金官桥战斗就开始了。
8月3日,日军第106师团加上伪保安队3个团,开始进攻。将炮兵阵地设在南昌铺,以山地少将指挥的第111旅团为左翼进攻金官桥,以青木中将指挥的第136旅团为右翼进攻马鞍山。
中国军队右翼金官桥主阵地守军是李觉的第70军,李汉魂的第64军为预备队。
李觉以57旅113团、114团及55旅110团一部分防守主阵地,以110团2营占领庐山土地庵高地,火力封锁右翼主阵地前沿地带,109团3营进驻牯岭,与防守庐山的保安团协力防止日军绕袭侧背。
金官桥阵地构筑了很多单兵掩体,用壕沟将各个掩体连成一体。壕沟上用粗大的原木固定,上盖2米厚的泥土,可有效防御飞机大炮的轰炸。日军在8月1日、2日两天都没出动步兵,以火炮和飞机对金官桥阵地狂轰滥炸,阵地都被炸成了焦土,但掩体内的中国军队没有什么损失。3日,日军开始用步兵冲锋,第70军官兵依托掩体展开反击,日军连续几次进攻,都遭到交叉火网的压制,伤亡很大。
4日晨,日军3000余人分三路向纱帽山及沙河南昌铺进犯。日军在牛头山与中国军队激战,日军伤亡400余人。入夜,李觉令109团3营从牯岭移动到土地庵上方鸡窝岭构筑阵地。这里山坡陡峭,居高临下,易守难攻,金官桥主阵地前敌人的一举一动都看得清清楚楚,用望远镜观察马鞍山阵地,也能一目了然。
5日一整天都在战斗,中国军队右翼被日军突破,老虎山阵地陷于敌手。
6日拂晓,中国军队开始反攻,第19师顾营尤为英勇壮烈,攻至该山,日军炮火极猛,顾营长及连长两人光荣牺牲,李营长奉命率队仰攻,全营士兵倍加勇猛扑进,13时夺回老虎山,恢复右翼阵地,并缴获机关枪5挺,毙敌200余人。这天,日军第113联队、第147联队向中国军队主阵地反复攻击,接着又用飞机、大炮对阵地狂轰滥炸,随后又是冲锋、激战、肉搏,阵地失而复得多次,形成拉锯,双方死伤均重。第113联队联队长田中圣道大佐,被当场击毙。山上山下及稻田中,敌我遗尸及武器很多,时值盛夏,阵地上臭气刺鼻,令人呕吐。
7日拂晓,日军将攻击重点放在侧面阵地,经过多次争夺,日军施放大量毒气,中国军队被迫撤至主阵地。第114团团长刘阳生率敢死队增袭反击时牺牲,官兵伤亡也很大。此后,日军连续几天向主阵地进行全面攻击,由于中国军队侧面阵地官兵撤回主阵地,主阵地火力大大加强,加上土地庵、鸡窝岭阵地居高临下,压制日军的进攻。为更好地发挥这处阵地威力,中国军队将第109团第1、第2营的迫击炮排都调上鸡窝岭,归第3营指挥。日军为解决中国军队鸡窝岭阵地威胁,连续四天集中炮火轰击,工事多被摧毁,多次派出敢死队冒死冲锋,每一次都败下阵来。为保卫鸡窝岭、土地庵阵地,中国军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第110团第2营营长刘咸宜、第3营8连田连长牺牲,伤亡官兵160余人。
此后多日,日军未能组织起有一定规模的进攻,只是小部队的袭扰和飞机轰炸,金官桥阵地呈对峙状态。李觉趁机一面加固工事,一面整编部队、调整部署。由于战斗减员过多,缩编了部分连队,将各团编余的班、排、连长成立干部队,将非战斗兵编入步兵连,充实一线战斗力。根据敌情判断,日军对鸡窝岭阵地势在必得,为加强守备,将55旅旅长唐伯寅调上阵地指挥,109团团长刘湘辅率第2营及2个团所属的干部连调上山,加强鸡窝岭阵地守备。
东侧战事趋于沉寂,西侧的战事却越来越激烈。
激战马鞍山
西侧中国军队的左翼,李玉堂第8军为守军,欧震第4军为预备队。南浔线西侧马鞍山阵地是冈村宁次点名要占领的要地,可想而知,这里战斗的残酷程度,丝毫不逊于金官桥阵地。
马鞍山紧靠南浔铁路,可以直接扼住南浔线。其西面左侧株岭山脉地形复杂,全是与马鞍山高度差不多甚至比它还高的山丘,丘陵间四通八达的道路通向岷山、瑞昌、长江南岸、赛湖、城门湖、七里湖、八里湖,每一处都有被突破的可能,制高点多、隘口多,防守难度大。随着战争进展,左翼防线上马鞍山、河洲上、磨盘山、岳母墓、十里山、蕉山口、大尖山、塔山口、狮子山、鸡公岭、杨家大山头、沙河火车站等处,都成为反复争夺的战场。
4日晨,日军第136旅团第145联队约2000人,凭借飞机的狂轰滥炸,占领沙河西南大尖山制高点,突入马鞍山,遭到中国军队第3师的果断反击,战斗至晚20时许,日军在伤亡600余人后败退。
5日7时起,日军以密集炮火向中国军队射击,随后坦克车前冲,遭中国军队坚强抵抗,激战于沙河、马鞍山各地。
6日,中国军队夺回大尖山。日军在猛烈炮击后,派出千余人企图反攻,中国军队死守不退,傍晚将日军击退。
7日,大尖山发生激烈争夺战,失而复得者六七次,中国军队团营长以下官兵伤亡超过千人,日军第145联队几乎全部击溃,两个团的伪军保安队经金官桥和大尖山的战斗之后,已经失去战斗力调往九江作警戒部队。
8日夜晚,日军再度调集兵力发起进攻,突入中国军队阵地一角,但很快又被第3师驱逐。在这次战斗中,日军第145联队长市川洋造中佐、联队副官木山武雄少佐、第一大队长荻尾佐藏少佐3人负伤,第三大队长内海畅生少佐战死。
9日晨,沙河西南方发生激战,日军向十里山、河洲上两地密集发炮,中国军队防御工事全毁。中国军队两个连的官兵坚守不退,全部殉难。中午,中国军队以精锐部队,绕敌右翼,猛烈反攻,并以两部包围正面日军,击毙日军数百人,迫使其退出河洲上。中国军队正在河洲上赶筑工事时,日军又大举增援来犯,战况更烈。磨盘山、蕉家山、狮子山(位于沙河西约2公里,并非蛇头岭南侧狮子山)进犯日军,已被中国军队堵击,退至田家汛一带。
据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全史》统计的数据,到9日止,日军106师团“各联队中、小队长伤亡约半数”,几乎失去了继续作战的能力。
10日晨,河洲上又展开激战。午后,中国军队再度反攻,克复河洲上各小高地。夜里,日军三四百人向磨盘山进发,被中国军队击退。
在开展阵地战的同时,李玉堂将部队编成以营为基本单位的诸多小股部队,从四面八方发动夜袭战,使得日军无法休息,不得安宁,一时间日军各处都遭到攻击,顾此失彼。中国军队连续战斗非常疲劳,伤亡也很大,13日,欧震第4军接替了李玉堂第8军的阵地。
第4军刚接管阵地便发动密集冲锋,欧震传下命令,进攻中如果军官后退,士兵可不用请示立刻击毙军官。在激烈的作战中,第4军从军长到排长,所有军官都战斗在队伍的最前面,团长和师长拿着手枪,挥舞着大刀参与肉搏战。日军本来就已经被第8军折磨得筋疲力尽,面对第4军凶猛的势头,只能仓皇向后败退,中国军队紧追不舍。
至此,西线也成对峙状态,双方都无大规模接触。
岷山阻击战
日军第106师团攻击停滞,8月中旬起,冈村宁次多次召开军事会议,命令第9师团从瑞昌进攻南浔线西侧岷山地区,继而攻击南浔线守军的左翼。
进攻岷山地区的主力是日军第9师团第6旅团长丸山政雄指挥的丸山支队,8月21日从九江出发时,有步兵第7联队、第35联队和1个山炮大队,26日、29日陆续增加了2个大队和1个山炮大队。
中国军队防守岷山的是王陵基第30集团军,辖第72军、第78军,有新13师、新14师、新15师、新16师,这支部队号称“双枪军”,士兵们一支“汉阳造”老套筒、一支长杆烟筒,武器低劣、战斗力较低。
8月下旬,日军对瑞昌不断增兵,22日在港口登陆,25日攻陷瑞昌。29日,日军增援瑞昌的部队已达1个师团以上。清晨,约五六百日军向新塘铺移动,在岷山大屋与中国军队发生遭遇战。这场小规模战斗,导致中国军队误判敌情。
30日晨起,岷山战事已经非常激烈。日军一上阵便出动飞机、大炮狂轰滥炸,第30集团军简陋的工事全被摧毁,伤亡惨重。轰炸之后,在日军攻击下,岷山阵地很快失守,立刻威胁到南浔路金官桥、马鞍山一线左翼安全。
对岷山日军的阻击,可谓一波三折。第一次,薛岳研判日军进攻岷山的是几百人,命令驻扎在德安的俞济时74军派一个团去阻击,很快就被击溃。随后,又派了一个旅,还是也没有效果。31日,薛岳直接电令王耀武率51师,当晚赶赴岷山。谁知,王耀武到达岷山时,日军增援部队也已到达,这时候日军兵力近万人。
74军军长俞济时是蒋介石外甥,作为中央军的嫡系和王牌,清一色德械装备,训练有素,是抗战时期中国军队战斗力最强的一个军,被日军称为“支那第一恐怖军”。两支精锐部队遭遇,很快就混战在一起。激战一天后没有进展,为了避免损失,王耀武趁天黑撤退到安全地带。
这时,日本广播、报纸上的新闻报道,泄露了岷山战事秘密,薛岳这才清楚日军规模和目的。沙河周边的形势一下变得严峻起来,薛岳一面命令第9集团军总司令吴奇伟指挥金官桥、马鞍山部队,迅速南撤至马回岭一线;一面命令俞济时74军全力以赴,阻击岷山日军,保证南撤部队安全到达指定地点。
经过两天两夜的鏖战,以第74军占领岷山,成功掩护部队撤退而告终。此战共歼灭日军2000余人,中国军队74军也伤亡接近3000余人。
沙河之战的战绩,战史中并没有确切的数据,1938年9月4日《东南日报》称:“敌此次在长江两岸激战大败……已死者5400余名,重伤8500余名……现留置九江伤兵医院者,尚有9000余名。”徐庚的《武汉会战》记载:“第106师团在整个金官桥的战斗中,一个师团16000多名官兵被中国军队歼灭了一半以上,共8000多人。”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统计了106师团截至1938年8月9日军官伤亡情况:战死大佐联队长1名、少佐大队长3名,负伤中佐联队长1名、中佐大队长1名、少佐大队长1名、少佐联队副官1名。
无论哪种数据最为准确,在沙河之战中,中国军队的将士们用生命护卫国土,视死如归的爱国情怀,永远值得我们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