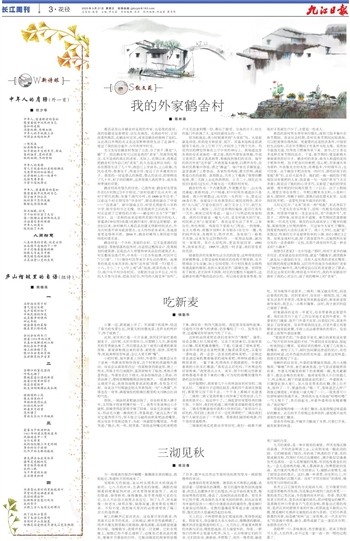■ 陈林森
都昌县苏山乡鹤舍村是我的外家,也是我的故居。我的祖籍是宜春靖安,出生在南昌。在我幼年时,父母流落到都昌,在鹤舍村定居,或者说鹤舍村接纳了他们,从此我以外甥的名义在这里断断续续生活了近20年,度过了我的部分童年、少年和青年时光。
先父先母在鹤舍村参加了土改,分了房子,算是“入籍”了。因此鹤舍村可以说是我的“老家”,但按传统观念,又不是我的真正的老家。实际上,长期以来,我都是把鹤舍村当作自己的“老家”,别人也是这样认为的。母亲在那里生活了几十年;我自己上学读书,上山砍柴,当民办老师,娶妻生子,两地分居,度过了许多庸常的日子。那里的一切是那么的熟稔,那么的亲切,即使暌违了几十年,村子的旧模样,还常常潜入我的梦乡,成为各种梦境的背景。
鹤舍村具有悠久的历史。已故作家、鹤舍村先贤袁作在《古村散记》中介绍说,“该村始建于东汉末年,成村于明代初期,发展于清代中叶,有1800余年历史。”以前这个村长期写作“学舍村”,据说清初就办了学堂——“浣香斋”。新中国成立后,村里长期驻有小学和中学,称学舍村当之无愧。但在我离开之后的某一年,村庄还原了它曾经的古称——鹤舍村(方言“学”“鹤”同音)。这一名称的由来是相传苏耽(传说中的仙人,晋葛洪《神仙传》有载)化鹤归来时,曾在这里栖留。新世纪以来,该村被列入都昌县创建文明新村的试点,作为古村落开辟为旅游景点,文人纷纷前来采风,各地游客更是络绎不绝。2016年,鹤舍村被列入第四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鹤舍村是一个古朴、美丽的乡村。它不是普通的因地制宜、零散错落的自然村,而是经过整体设计、统筹规划的建筑群,呈现出古人智慧和审美品位的建筑艺术。村庄整体呈曲尺形,中央有一口长方形池塘,村民叫它“门口塘”。门口塘给村民带来许多生活的便利。池塘养的鱼是大家共享的,每年“还年福”的那一天(腊月二十八,月小二十七)早上竭“泽”而渔,收获的鱼大小搭匀,按户头平均分给村民。分配的方法公平公正,叫号的人不参与分鱼,把鱼分好后,叫号的人按名单“盲叫”,户主无论拿到哪一份,都乐于接受。分鱼的日子,村庄的巢门外挤满了人,是村民最快乐的一天。
因为距离近,我小时候喜欢到“大堂前”玩。大堂前就是祠堂,有的地方称祖堂、祖厅。其基本结构是前清留传下来的,分上厅和下厅,中间有上下两个天井。列祖列宗的牌位供奉在上厅中央的神台上。我知道这里有我的母系家族的一席之地,我的外曾祖袁铁梅,外祖父袁训芷,舅父袁武扬等,都能找到他们的名讳。每年的农历年底“还年福”,年夜饭基本就绪,以锣声为号,全体村民都集中祭祖,谓之“捧盆”。每户家长手捧饭盆,盆里盛满了三牲祭品。各家纷然鸣炮,震天价响,满屋都是白色的浓烟。浓烟散去,天井上下堆满了厚厚的鞭炮屑,第二天踩上去还热烘烘的。正月二十,则在此为祖宗(始祖)过生日,外嫁女这一天都回村庆祝。
鹤舍村作为一个古建筑群,外观整齐划一,山头凤尾叠起,栋栋相连,户户相通,村中间所有通道由石条铺成。我小时候数过,由村的一头到另一头,要走过18条石巷。房屋设计具有典型的江南民居特色,其中的“大八间”,厅堂分前后厅,前厅又分上下厅,前厅左右各正房一、厢房二,后厅还有两间偏房,前后厅各有一天井,厢房之间有甬道,一扇小门与两边的房屋相通。我的旧居就是一幢大八间,是全村最大的厅堂,村民称之为“正屋堂前”。我在这里生活了多年,三家合住,相处和睦。鸡窝在下堂前大门两边,一到傍晚,女主人喂鸡,将瓢中饲料(多为稻谷)往空中一撒,鸡们闻声而来,各拥其主,秩序井然。各家房门一般都不关锁,从未发生过财物纠纷。一家用品短缺,就向另一家借用。有什么好吃的,更是有福同享。1981年,我举家乔迁。1995年,我因一时手紧,将旧居变卖给邻居。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这种传统的民居渐露弊端,主要是地板和鼓皮的结构不便装修,也不便增添卫生设施,加上空间受限,不少村民都在公路两旁建造新的楼房,有的人家甚至开门面做生意。但即使有了新居,老宅却并不拆除,村庄的完整性不能破坏,这是鹤舍村最严格的自治公约。所以现在游客来参观,发现村子里面住户少了,主要是一些老人。
都昌的农村男女青年举行婚礼,按照习俗多集中在春节期间。农业社会时期,农村在春节期间比较清闲,可以把喜事办得热闹。更重要的还是经济条件,中国农村生活俭朴,只在年节期间才有条件大吃大喝。虽然如今温饱无虞,但传统习惯被传承下来。如今,打工者也多选择在春节期间返乡。于是,春节期间,便是新婚夫妻最喜欢的好日子。鹤舍村的美食,最为人称道的是饺子粑和年粑。饺子粑也叫炒粉粑、馅心粑,用普通大米为原料,外表像北方的水饺,皮薄馅多,平时做早点,也可待客。由于做饺子粑没有统一的时日,那些好面子的家庭“煮”妇,正好大显身手。她们把一碗一碗的饺子粑端给没有做粑的人家,收获着一句一句的“难为”(方言多谢),既见证了她们的心灵手巧,又彰显了她们的贤良淑德。做年粑的时间都在腊月二十以后。由于工程较大,需要左邻右舍帮工。年粑以糯米为主料,小茶杯口面大,圆饼状,用模子刻印,蒸熟后浸在腊水缸里。从前我们吃年粑,一直要吃到来年栽田的时候。
儿时记忆中,“文革”前有一种“唱曲”,形式类似于曲艺,一个老头在音乐伴奏下,说唱一些粗俗而搞笑的故事。村里很早就有一支业余乐队,有“洋鼓洋号”,有笛子、二胡伴奏,前面还有开道旗。春节期间若逢婚嫁喜事,一时风光无限。现在的乐队成员穿上了整齐的制服,新娘则披上时髦的婚纱。不过如今大家忙于赚钱,围观看热闹的人没有以前多了。我十几岁时,也滥“笛”充数过,吹奏的无非是旋律简单的小调,如《小桃红》之类。如果是他村礼请,除了酒食款待外,还能得到东家分发的一盒香烟和一元钱,在那个清贫的年代是一种妥妥的“小确幸”。
我曾在《老家》一文中写道:“那时,相对于求学的城市而言,老家就是母亲的怀抱,就是‘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就是从小濡染的方言。没有人追究我的老家在哪里,他们都把我度过寒暑假、过旧历年的地方当成我的‘老家’。”20世纪80年代,我与靖安县山区的老家建立了联系,但在过去很长时期,特别是少年时代,我的外家鹤舍村填补了我的心灵空白,成了我的精神上的“老家”。